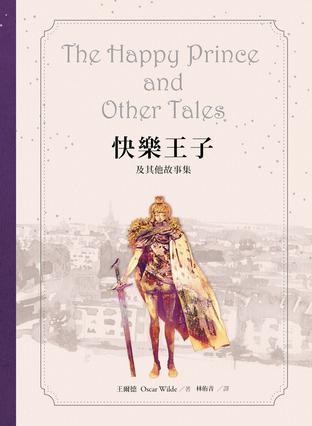「過好日子,把日子過好。」
有的時候,事情只要換位另一個角度思考,就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跟理解,也會有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民國76 年解嚴之後,雖然開放可以回大陸探親,但外省第一代已經回不去了,過去的家已經人事全非,到凱凱這些外省第二代時,也就覺得沒什麼差別了,不會再覺得該「回去」哪裡、該「去」哪裡,反而是台灣這片土地才是成長的家,家人們都在這裡,這也就是家了。人們因為時局而相聚在這裡,小老百姓的,也只是希望努力把生活過好,衣食無缺,代代相傳。不管未來如何,會往哪裡或該往哪裡去,也只是希望我們兒孫在這塊土地上過好日子、把日子過好而已。